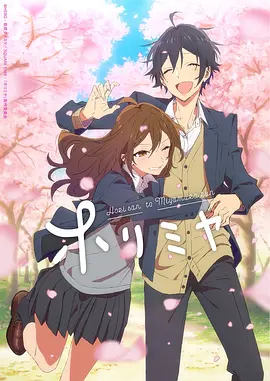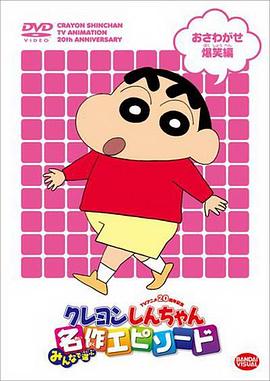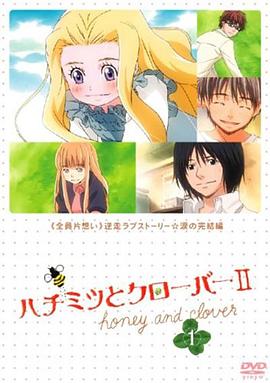剧情介绍
如果是经常看少女向动漫的大家一定对《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和《开花物语》这两部作品耳熟能详,而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心灵想要大声呼喊》,正是制作了这两部动画作品的制作团队制作的。这部动漫是由长井龙雪执导,冈田麿里编剧、a-1 pictures制作的一部动画电影。
而我认为,之所以成濑的语言能力被封印,归根结底都源于童年创伤,童年创伤导致她自己幻想出蛋先生,封印了自己的语言能力,才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事情。童年创伤对小孩的影响程度之深,在他们未察觉之时,往往会影响其自我认同。这部动画我已经不想吐槽情感线的凌乱了,但抛开情感线,从童年创伤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部动画的情感表达还有细腻程度都是一部上乘之作。很多人拿这部动画和《声之形》作对比,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动画的制作时间比《声之形》早2年,并且在设定方面和《声之形》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仅仅是因为都是失语这个特征,未免也太过草率。
前面提到的,我认为这个故事的主线依旧是以女主的成长为主线,男主坂上虽然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并不想花费笔墨在男主角身上,成濑身上更能挖掘出一些东西。这些事情的开端是因为成濑的失语,而埋下这根线的诱因正是因为童年创伤。
今天的主题就借着这部动漫聊一聊童年创伤对人的影响和反思。
痛苦的童年为神经症埋下源头
幻想自己是公主,并且想要拥有一位王子来迎接自己的戏码,是不少小女孩内心的幻想,成濑也不例外,她是一个天真开朗,喜欢和人交流的小女孩。在山上有一座“城堡”,而这座“城堡”其实是爱情旅馆。某天她看到父亲从那座城堡里出来,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爸爸就像王子一样从山上的那座城堡出来了。一语成谶。父亲和母亲分开了,父亲走之前,扬起一抹意义不明的笑容对她说:“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你多嘴所造成的吗?”
其实在心理学上,成濑的这种无法再开口说话的行为就是神经症的表现,这些形形色色的,难以理解的神经症症状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几乎每一名这样的神经症患者都想要消除这些症状。成濑虽然是自己选择了不开口说话,但她不说话的时候同样痛苦。神经症又名神经官能症,是最常见的心理疾病,患者有持久的心理冲突并为此深感痛苦,但其戏剧性的症状常缺乏明显现实意义,而且没有可证实的器质性病变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思考特.派克在他的《心灵地图》一书中宣称:神经症症状本身并不是病,而是治疗的开端,它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目的是唤醒我们展开自我探讨和改变。
患者也罢,周围人也罢,很容易关注患者富有戏剧色彩的症状。不过,按照精神分析的概念,虽然患者为神经症的症状痛苦不已,但这只是一个象征,问题的核心在于患者的一些创伤体验。只不过,这个创伤体验主要并不是源自此时此地的创伤事件,而是产生于幼年发生的一些创伤事件。
当时,对于眼中缺乏人格力量的小孩子来说,这些创伤是”不能承受之重“,如果直面它会遭遇心理死亡或实质死亡。所以,幼小的孩子会发展出一套特定的心理防御机制,扭曲创伤事件的真相,将其变得可以被自己所接受。从这一点上讲,,神经症是一种保护力量,课保护幼小的孩子度过可怕的童年灾难。
成濑的童年可以说是很难用美好来形容,父亲的话语就好像魔咒一样围绕在她的心间,彼时,她尚且年幼,那句话是对她自我认知的否定,她用自己尚浅的的生活经历给自己塑造成为了一个充满幻想,能用自己的话语给他人带来幸福的自我,但父亲告诉她,她的语言是伤人的利器,无法给人带来幸福,只会给人带来灾难,差不多就是把她全盘否定,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于是她产生的防御机制就是,不再说话,看似荒诞,实则合情合理。
美国心理学家四考特.派克认为,这是生命的一个秘密,童年的痛,弱小的我们无法承受,必须扭曲以保护自己。但当神经症真正展现的那一刻,我们其实已经长大。这就好比是,戏剧化的神经症状在提醒我们,喂,你长大了,有力量了,别逃了,现在是正视童年那个不能承受之痛的时候了。
于是有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被压抑的愤怒变成了焦虑
成濑的母亲独自抚养她长大,在日本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因为婚姻的不幸而又重新踏入社会,压力可想而知。在片中,母亲不允许成濑出现在人前,因为一个不能说话的孩子,会引起他人的非议。成濑开口说话腹痛进了医院后。母亲站在她面前,很无力的说:”太差劲了!又是那个莫名其妙的蛋的能力吗?!你就这么恨我吗?到现在你都不肯说话是吗?“这一连串的质问,成濑一直握紧双手,低垂着头,没有说话。
可能是她看到母亲的压力更重,而她的自我认知里也明白,不能把矛头指向母亲。所以她不光”封印了“自己的话语,还把自己的愤怒压抑下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她所承受的压力越大,在她心中产生的攻击就越多。但是这些攻击性,她在家中根本没有机会表达,只能压抑到潜意识中去。她这是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罢了。并且可以料想的是,以后她对自己的愤怒感只会越积越多,但其实还是对父母的愤怒。
所以,当她在门外听到了坂上对仁藤的告白时,她的心中一时间无法接受,而且还有一种无名的愤怒。但是,她的心理机制注定不允许她表达愤怒,所以只能用焦虑的方式表达出来。潜意识里的那个源自童年时的”脓包“,即语言是伤人的利器这种类似的场景所激发。所以她选择了逃避,明明是自己那么想要当女主角的音乐剧,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告白,她选择了逃避。
此时的她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怀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即使我不用语言来表达我的心,用其他方式表达还是不行吗?她焦虑的根本在于,她想找一个罪魁祸首给自己的结果负责,倒头来根本找不到,她不知道现在的局面,舞台的缺席,家里关系的恶化,到底应该怪谁,明明自己已经不说话了啊。这才是她焦虑的根本。
而在这部动画最妙的点在于,男主角坂上他明白了成濑的焦虑,他知道了成濑的焦虑只是因为对他,还有周围一切的愤怒,他让她用言语来伤害他,成濑说出了潜藏在心底里的话。
这正是德国专家螺丝霍普特说的,”哀悼“。坂上慢慢引导成濑说出,确切的说是吼出心里的话就是让她把潜意识里的攻击性转移到他的身上。然后承认自己童年的不幸,接受这个事实,最后和这个悲剧说一声再见,就像是哀悼自己一个逝去的亲人那样。那样一来,她的愤怒情绪就会得以宣泄,潜意识里那个“脓包”就会消失一大半,并且“焦虑=愤怒”这种神经症式的心理公式也会被改变。
我们的社会更喜欢好孩子
正如成濑的母亲那样,我想不管是哪个国家的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听话,乖,不要做一些让父母为难的事情。但,听话的好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如父母所愿我已经停止了不胡闹,不说话,为什么你们还是不满意。
成濑小时候滔滔不绝的样子成了她的阴影,她不再说话了,成了她心目中的好孩子了,却依旧得不到母亲的重视。
我们的社会,文化,就是喜欢好孩子。
心理学家胡慎之说:”经典的好孩子,在家里听父母的话,依赖父母,在学校听老师的话,依赖老师。这样一来,这个孩子的独立空间会受到挤压,他会觉得不是为自己而活。于是就缺乏动力。他可能会出色的完成家长和老师交给他的任务,但却表现得比较麻木,对很多事情都缺乏欲望和追求,这也是抑郁的 一种体现。“
不正是成濑的表现吗,她已经是一个好孩子了,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让母亲少一点担心,不说话,害怕说话母亲就不开心;对母亲的质问从来不反抗,因为她觉得反抗的话语一定是伤人的,她不愿意伤害她的母亲。
动画的开头,成濑一脸阴郁的打开门去学校上课。她呆在学校也是无所事事的在草稿本上绘画,画着她想象中的鸡蛋先生。她是缺乏激情的。因为,她努力学习也好,按时上学也好,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为了满足母亲的期待。这种刻意的努力,是一种强迫性的努力。母亲要时刻提醒她,她也要经常督促自己,才能继续努力下去。但是,他们仿佛对努力来的结果,譬如好成绩等都没有什么热情。
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北京教委会出台的新规定,禁止学校和老师给小学生布置作业。本是好事,但却引出了很多家长的焦虑。多家媒体报道,他们不知道,除了学习,还能和孩子谈什么,如果没有作业,孩子的时间应该怎么打发。不用来学习,孩子不会学坏吗?
有作业也好,没有作业也好。我想我更关注的是,父母和孩子真的不能够构建起深刻的情感链接吗?
每个人都孤独,而打破孤独的唯一答案是,能与其他人或其他事物构建真切的链接,也就是有人情味的链接。
情感链接,是最真切的链接之一。但中国人羞于谈感情,其实是内心对爱绝望,结果是,父母不能与孩子进行流畅的情感交流,而只能进行语言层面的交流。语言层面的交流即思维层面的。身、心与脑三者中,头脑层面的交流是最靠不住。《圣经》中写道,人类齐心协力想造一个通天塔,上帝为破坏他们的努力,叫他们学会说话,但学会说话后,他们便起了争执,通天塔就修不下去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没有语言,人能通心,从而可以建立真正的链接;但有了语言,就割断了心,人们都以为自己的语言是正确的,因而起了争执。
简单来说,执着于头脑层面的链接,其结果是,你要符合我头脑的想象,你要与我语言要求你的一模一样,这才是我的好孩子。
我想这也是成濑以及其他好孩子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