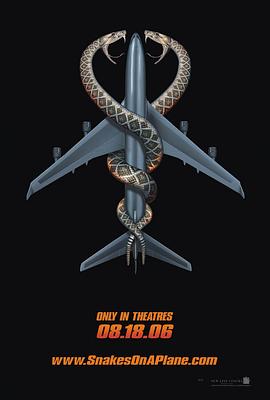剧情介绍
本故事已由作者:西妩图,授权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发布,旗下关联账号“”获得合法转授权发布,侵权必究。
她又做了那个梦。
梦中是一个张灯结彩的夜。
她盛妆红喜裳,站在玉萝树下等一个人,等到月宫西下,朝晖烈烈,可没有人来。
她只听见了厮杀,她只望见血雾之中,一个愈行愈远的背影。
1
阿幸是魂相宗第七百八十九代唯一传人。
这名头很是唬人,可架不住她还是个未出师的,到了人间也只能在一家灯坊打短工。因着老板芙白目力不佳,故而入夜后,往往是她独自当值。
这晚,眼瞧着月宫归西,东边也隐约有了亮,一如往夜的,半个客人影都没见着。阿幸打了个哈欠,昏昏欲睡地看着从隔壁书坊借来的话本子,连客人进了门也不晓得。还是迎客灯看不过眼,“咚咚”地把自个儿往墙上撞,才惊动了她。
阿幸抬头一瞧,原是一位额间绘了红色玉萝花的妙龄少女,容色灼灼,眼沉秋水,周身似围绕着一层散不开的冷气,睇过来的那一眼,直教人打了个激灵。
阿幸困意顿消,站起了身,笑问一声:“姑娘买灯?”
那姑娘不答,打量着她,许久后开口,声音也如冬雾一般清冷又缥缈,“你是阿幸?”
阿幸诧异地眨了眨眼,问:“你识得我?”
姑娘摇首后又颔首,道:“有人说只有你才能帮我。阿幸姑娘,传闻魂相师能上通天地鬼神,下观万物生魂,是比肩三州神明的术师,可是如此?”
这个传闻,阿幸也是来了人间之后才听说的,当时便大吃了一惊。不想在玉沧山门中已经沦为末流宗门的魂相宗,竟还有如此好的名声。也不知是哪位好心人做的这般虚假宣传,着实让魂相师脸红。
阿幸脸颊微鼓了鼓,有些不好意思地道:“不过是江湖传闻罢,做不得数。像我这些年所学的,也不过是些引魂入梦之术,还十分浅薄,怕是帮不了姑娘。”
“可我所求的,正是一个梦。”姑娘淡淡地笑了,她从袖中翻出一块黑色令牌,推至阿幸的面前,道:“而这是我的酬劳——”
那真是一块毫无特色的令牌,看着锻造工艺比街头铁铺的还敷衍。
阿幸凝神望了片刻后,杏眼却弯成了月牙,温声细语地请她在厅中长桌旁坐下,客气地问:“那姑娘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姑娘姓徐名阮。
阿幸听过这个名字。
这段时日,玉萝城的新城主愿用千年玉萝果换得一梦的消息传出后,便有不少奇人志士从三州各处赶来,街头巷尾都是议论纷纷,连带着这位城主大人的名讳也传了出来。
说起来,阿幸还去参加过她的即位大典,可惜当时离得太远,没瞧清这位年轻的玉萝之主长如何模样。
彼时,一同观礼的书坊老板明九恣还同她八卦过,说南州诸城里大祭司与城主神权分立,可这玉萝城却不知为何在二十年前竟是取消了大祭司。神权于一身的十七岁女城主,不可谓不是南州诸城里的独一份。
却是没想到,这独一份也有独一份的不顺意。
“我不是想要一个梦,而是想入梦一观。”徐阮轻笑,目光飘向桌上的某一点,“说来好笑,这个梦我夜夜都会梦见,每每醒来时,都心痛如绞,泪流满面,可又始终不记得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梦。”
2
这对于一个魂相师而言,并非是难事。
魂相师魂相天地,其中人有三魂六魄居灵台,过往归识海。阿幸想了想,便想得很清楚了,只要徐阮愿意献出一点指尖血,供她去她识海里翻一翻那些过去,定能找出那一场如鲠在喉又记不清的旧梦。
只是这是她第一次帮人相魂,说不准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徐阮听了阿幸的顾虑,漫不经心地笑了,冷眼觑着这位年轻魂相师,道:“总不会让我傻了吧。”
阿幸认真地道:“那倒不会,只是有可能会让你彻底忘记那场梦。”
徐阮怔了怔,微微一笑,道:“若是想不起,能彻底忘了也好。”
阿幸按捺下不安,待徐阮往那杯中滴了几滴血后,便闭眸念诀。只见那杯中浅浅的一层血,突然逆空而上,化作一只红色小兽。那小兽象鼻犀目,如牛尾的尾巴一甩一甩,将寸高的魂魄阿幸甩到了背上,朝对面姑娘的额心冲去——
然后连人带兽如一同跳进了饕餮的口中,半点挣扎都没有地落进黏重深厚的黑暗里。
万物寂静。
外面的徐阮还在一无所知地等着,她胸腔里又涌起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燥意,疯魔一般赤红了眼。她下意识地摸到腰间的玉萝酒,仰头倒了半壶,玉萝酒凉,寒气一层一层叠了下来,终是冷静了下来。
年轻的魂相师再睁开了眼时,其实并没有过去多久,可徐阮在对上她的目光,却觉得已度数个春秋。
徐阮不知为何心生怯意,默了默,方正了容色,问道:“阿幸姑娘,如何了?”
“阿幸姑娘?”年轻的魂相师似觉新奇一般轻轻笑开,又置之不理。她展袖左右打量着,面上嫌弃神色一闪而过,最后将宽大的广袖往上捋了捋,方又露了笑,答道:“徐阮姑娘,是想用这玉沧令换一个梦?”
徐阮心生怪异,淡声道:“若是这块令牌是阿幸姑娘所说的玉沧令,那便是了。”
阿幸轻轻叹了一口气,“命中注定了罢。”
徐阮莫名,阿幸却招了招手,白影一闪。
徐阮顿觉脑中一轻,只见一匹白色小马驹伶俐地从她额心跑出,它口中衔着一个小光球,稳稳地甩进了飘浮来的一盏红灯笼里。
徐阮眉头微蹙,目光隐含锐气,“这是何意?”
阿幸微微地笑了,“此为取梦。接下来,就需要姑娘离魂了。”
话音刚落,徐阮眼皮一重,困意来势汹汹,她不自觉地倒向桌上,却在额头磕上桌的前一瞬被接住——那是一只极柔软的手,和一个极温柔的声音。
那是阿幸的声音,在黑暗里回荡,她道:“徐阮,这是有人好不容易求来的机会,你可要好好珍惜……”
徐阮努力辨清着那愈发模糊的每个字眼,可那声音越来越远,最后只剩下眼前飘来的一点亮光。
在她伸手碰触的那一瞬,传来一股拉力,就那样一拉,她便往那处飘了去,似去雾中,做了一场颇是有趣的梦。
在梦中,她也姓徐名阮,也有一个当玉萝城城主的母亲,这位母亲也有着一身让人亲近不起来的本事,同样不大待见她。徐阮早已习惯安静地待在自己院子里安静长大。
可来到这儿的第一日,她就发现这个徐阮,实在是又与她不大相同。
她每每一开口说话,如同枝头上所有的麻雀都开始唱歌,吵闹得很。可徐阮也没法子,就好似在同一个躯壳里有两个灵魂般,一个安静,一个活泼,如今却是活泼的那头赢了上风。
安静的徐阮只能破罐破摔地跟在小伙伴的身后,做一些曾绝不会去做的事情。今日打鸟,明朝摸鱼,后日摘果……在这梦中总是有那么多热闹事可以做,也总有那么多快乐事可以笑。
时间久了,徐阮也生了些许趣味,梦外那些种种竟渐渐忘了,却是安心地做了那个爱偷偷往外溜的小徐阮。
3
梦中日光弹指过,一晃小徐阮长到了十四岁,她的母亲宣布重启祭神大典,而担任司巫祭神之职的,便是她徐阮。
却不想,会有刺客从天而降。
也不曾想,会有一人斜里飞来,身若游云,势若惊龙,救她于千钧一刻。
所有人都似被煞住一般,只晓得愣愣地望——
飞红万叠花成雨,夹杂着从剑上洒落的血光,只听得金戈脆断,又见得寒星闪闪。在那铺满了碎红的祭台上,谁也未望见,这是命运的拐点。
只因他们的初逢,实在是像极了话本子里的那些英雄美人的故事,道的是金风玉露一相逢,四目相对的那一须臾,似刀光剑影都化作漫天流星,归尽千山万水的雨珠露光。
一见钟情的戏码,就像三州的神明,人人都想遇见,人人都以为能遇见,但是总是遇不见的,那永远都是别人的故事,也永远这般动人。
等她回过神来时,她已从侍女口中打听来了他的名字。
裴绥。
徐阮想,这可真是个好名字。
他是城主府里新来的侍卫。府里无论年纪的女人们见他时脸红,不见时又常常议论他,甚至连原先惫懒的老婆子都开始热衷当值起来,只是盼能与那裴郎匆匆过一面,说上两句。
可是他是那样的冷,又那样的远。
他从不与不相干的人说话,也从不另眼相待任何人,就似一座高高山巅,不可攀。古往今来,总有人想要去舍命攀一攀高山,不顾生死。这也是一种令人心折的魅力。红尘男男女女,见到这样的人,也会不顾一切地想去试一试,试一试自己可能就是那位特殊的勇士。
很难说,她会在裴绥的这座高峰上屡折不挠,是否也是因着这样的心态。
这情动来得又急又快,好似命中注定一般。她想着横竖不过一个梦罢,索性随心而动,倒是干出不少出格事,平白惹了不少笑话。
但总归还是有些用处的,她制造了无数次的交集,终得与那高山裴郎,系上了红线。
她约他在花神殿后的玉萝神树下见面,她盛装打扮赴约,又提早了好些时候。隔墙传来的笑语声教她烦扰焦躁,墙又是如此之高,教她望不到,那裴郎来了否?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她竟是爬上了树,只盼能望见谁的踪影。
可望见的,只有那墙下经过的人成双成对影,一对走过又走来一对。
也不知多久,似乎很久,也似没有很久,等得她眼泪都沾湿了衣裳。
终于,那裴郎来了。他行至树下,发现了正抱着树无声哭泣的她,仰头问道:“阿阮,你怎么到树上去了?”
她垂头见是他,却是委屈极了:“你怎么才来啊?”
话说完,却又是悔了。
她想着这么个无理取闹的小姑娘,可真不似她徐阮。
诚不想,那钢铁一般冷硬的裴绥弯了眼,道:“前些日子,我翻了翻你留在我那儿的话本子,上面说,春时四月首,飞花漫天,或是冬日十一月,小雪微醺时,少女从天而落,落入院外的少年怀中。”
树上少女的脸渐渐红了,心中方寸若有晴天雷鸣,她缠着衣角,移目左右,道:“我不太能听得懂你的意思。”
“可惜玉萝城春日没有飞花,冬日也无落白,少女只能怀揣着满腹心思,坐在树上唉声叹气。”裴绥抬头望她,似笑非笑地道:“阿阮,你觉得这个故事如何?”
徐阮差些气得仰倒,鼓着脸囔囔道:“我才没有哀声叹气呢!”
却是腿上蓦地一软,脚上一滑,从树上落了下去。
徐阮不管不顾地尖叫起来,却又短促地停在了半途。
只因,裴绥接住了她。
眼角还泛红的少女睁开了眼,露出那如玉石一般的眼睛,如同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亮晶晶地看着他,如同看着降世的神明,“你接住了我!”
裴绥失笑,道:“不然如何,任由你摔个头破血流么?”
那是怎样清光明艳的一笑啊。
笑得少女失了心智,只是愣愣地,灼灼地看着他,道:“裴绥,你是从天上来的,还是我梦里来的?”
裴绥眼不自觉地弯了,一本正经地道:“我是为你而来的,阿阮。”
4
花影又坐前移。
时至玉萝城一年一度的“萝月夜”,涌向街头的玉萝城民们会手提各式明灯,在飘满飞花的夜晚各处游玩赏灯,行至东边的花神殿里,折花献神,祈福来年,等到天亮时,人们才会散去,直到新年朝阳初始。
这日傍晚,城主登北坊楼,和楼下的城民共待月宫东升。鼓声三响时,一队扎满红绸的喜车也缓缓从城主府驰出,有人随街洒下喜钱,高声喝道:“城主今日嫁女,与尔同庆!与尔同庆!”
如此繁盛的夜,城主府虽是张灯结彩,却是冷清得有些过分。唯有新娘院门外,剩下零星的几个侍女守在新娘院门口,听着遥遥传来的欢笑声,愈发心痒难耐。数着时辰未到吉时,便纷纷凑到墙边,你抱我,我抱你地试图往外望。
徐阮盛妆红喜裳,探首问:“你们在望什么?”
“小姐希望我们望到什么?可是望那来迎亲的礼车到了没有?”年轻的侍女们也不惧,纷纷捂嘴笑了起来。笑得徐阮跺着脚,作势要来掐她们的嘴,才又道:“好了,小姐您快回去吧,吉时将至,您望了许久的裴郎,可是要来了。”
这样喜气洋洋的日子,不合规矩的轻佻调笑,也不会真教人生气。她心里漫过甜意,面上虽是羞恼,脚下却是乖乖地回了院,只等那唢呐声到她家。
可是她的心又这般彷徨,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在纠缠不休,如此笃定裴绥不会来,但是又有个声音在告诉她,她的裴郎一定会来。
星月齐辉,夜空明净,她刚转身,就看见那骑墙而来的红衣青年,跃下时还有些踉跄。
突涌上心头的心酸和欣喜,教她眼间一热,不知为何竟是生生涌出泪来。她隔着泪眼,遥遥地看着那个衣领松散歪斜,金冠摇摇欲坠的青年一步一步朝她走来。
玉萝城的飞花那样美,他印在额上的吻那样的烫。
他含笑要拥她入怀,说着世间最动人的情话:“阿阮,我来了。”
可是来不及,她来不及听到,便已成烟雾般在他怀中散去。
玉萝花在此刻似到了花期尽头,无需风来送,便纷纷跌落枝头,落在他的衣上发上,如同一场没有征兆的大雪。
他怔怔地看着空无一人的怀,低声唤:“阿阮,我来了。”
从树后绕出一个穿着时下并不流行的深袍广袖的少女,她望了望天上的星色,又望向红衣青年,道:“不必唤了,我已经将她送回她该去的地方了。”
“不!时间还未到,我们还未拜新婚,还未白头相守……”裴绥的脸颊有些抽搐,眼底通红,饱含怨怼,道:“为什么!你承诺过,我付出灵魂的代价,你就会让我与她在梦中相守一生……”
“因为她此时不回去,便再也回不了了,你难道想让她和你一样?”那少女无甚真心地弯了弯眼,道:“而且,这个也不能怪我。我哪会知道,她竟是拿的一块没甚用的令牌做的报酬。若没有第二枚千年玉萝果支撑,这个时间通道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况且……”
少女带着深意打量着他,道:“况且,裴先生是不是已经忘了,当日你用灵魂到底换了什么?”
如遭雷击。
裴绥如玉的面庞沉寂了下去,愈渐明亮的天光却照不亮他身上的阴影,他失力地跌靠在花树上,“我记得,只是……我以为我能在她生命里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
少女不耐,冷道:“没有只是。她醒来之后只会以为是做了一场梦,没有人会把梦当真。”
裴绥彻底沉默下去,他闭上了眼睛,想起前世的彼时。
5
那时,他从仇人的手中夺回了曾被夺走的一切,成为了玉萝城的主人。
可是年少时那个从树上一跃而下的明丽少女,却变成了午夜里如影随形的阴影。等他再次见到他的阿阮时,唯一将他们联系起来的,只有她手中的那把贯过他胸膛的长剑,和她眼中的昭然恨意。
他没有杀了她,他将她留在了身边。
他知道她恨他,他杀了她的母亲,她的恨理所应当。他无谓地放任,甚至纵容。哪怕她的每一次迎合,每一次微笑,都只是为了杀了他。
不久后,有人送来和她模样相似的女子,在宴会上奉上,她怒而离席。他终于窥得能引她破冰的方法,开始不计代价地搜寻三州里与她相似的女子——这些女子灵动,活泼,看向他的目光里只有灼灼爱意,如同能罂粟一般,让他开始觉得疲倦,让他沉溺逃避,让他每每都以为又回到了那玉萝花开的年月。
可他又无比清醒,那年月早已过去,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他的阿阮,也再不会回到他身边。
难以介怀的爱与恨将人变成了怪物,他和她都在相互撕咬,谁也不肯先一步放弃,除非其中一方死去。他在某一日醉酒后,终是厌倦了这日复一日的痛苦,他毫不留情地将她甩在地上,连同那把插入了他肩胛的匕首。
他醉醺醺地冷嘲:“怎么,都这么久了,还是连刀都拿不稳吗?”
她跌坐在地上,垂着眸,面上笼着晦涩不明的阴影,让人心底发冷。
他最不喜她这个表情,这个会让他心中抽搐的表情,而这一次醉意蒙蔽了他的理智,击退了他的耐心。他轻佻地捋过她颊边的碎发,问:“还是说,这是你想引我注意的法子,就如同当初那般?”
她面色大变,近乎不可置信地看向他,眼中迸裂出似可割裂肌肤的锐气,她冷笑着注视他,“我只想杀了你!”
他不置可否,得意地道:“可是你爱我,所以你不会杀我,以前不会,以后也不会。”
她如蒙重击,无法言语,良久后,如同一朵枯萎的花,不堪重负地垂了下去。她低低地笑了起来,“是啊,哪怕明知你爱我,你说会娶我,都是在骗我,只是为了利用我,可我竟然还可笑地对你心怀着一丝希望……”
她挣脱出他的手,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再次紧紧握住了那把匕首。
可是这一次匕首,再对准的,却是她自己的脖颈。
他想要阻止她,可是醉意麻痹了他的神经,那一步终是迟迟。她遥遥抬眉一笑,手起刀落,没半分盘旋,也再留下任何只言片语。
鲜血从她的脖颈喷溅而出,溅到他眼睑上,他颤着手想去捂住她的伤口,只是徒然,血液又从她口中呛出,她艰难地侧过头,放佛在躲避他的碰触。
他想说,阿阮,我又骗你了,阿阮,我爱你,我想娶你,无关仇恨,无关野心,只是因那日你笑着走向我……
可是他一个字也说不出,他只能更深更紧地抱住他的阿阮,更深更紧地将自己放逐在夜深里的阴影里。
微风送来玉萝花香,方知又至冬日。
6
来年的时候,他贴出告示,愿用千年玉萝果来换得与亡妻相见的机会。三州奇人志士纷纷来此,却毫无办法,直到有一位自称“昼先生”的术师告诉他,南州诸城的祭司皆以凡人之身承了神使,是不入生死九渡口之魂,不入轮回,没有来生。
只有拿着这千年玉萝果去风雪渊头求求天下第一魂相师,或许还能有相见的机会。
他走过三千里日冷冰封,翻过三千座大雪压山,穿过朔风也吹不散的云雾,终于见到了天下第一魂相师。
魂相师问他,若是见了,又如何?可是见了,便能弥补她这一生痛苦缺憾?
他无言以答。
魂相师又问他,若是能付出灵魂的代价回溯时光,用他的死亡换她重来一生。这一生她太平诸顺,平安喜乐,另结良缘,他可否愿意?
他怎能不应,这怎能不应?
冬风如此悲凉,又如此浩大,吹碎了月光,吹熄了四散的荧光,前世今生此间一梦都在旋转中支零破碎,包括那个穿越时空来见一见爱人的那个青年。
魂相师淡淡地看着他,犹如九天神明俯下的一瞥,渺渺无声,“还是说,你后悔了?”
“不悔的。”裴绥看着逐渐透明的手,吐出胸腔中最后一丝热气,笑了,“是裴某一时贪心作祟,此间一会,本就是多求来的。”
世间彩云易散,好梦易醒。
他于昨夜离开人间,走时面带微笑。
她于今晨重生人间,醒时脑中空空。
阿幸还在黑暗里挣扎不得脱,幸好有人在额心猛地一弹,竟是顺势魂归灵台,睁开了眼。
天光已是大亮,她觉得眼中甚涩,有些不适地眨了眨眼,看见对面的白衣女子,不由有些心虚地蹭了过去,道:“芙白,你不知道,我刚刚做了一个梦,细数起来,这还是我长这么大做的第一个梦。”
对面的白衣女子眼覆青纱,闻声抬头,颇是配合地问道:“那你梦见了什么?”
阿幸靠在她的肩上,闭目道:“我梦见我成了天下第一魂相师,住在风雪渊头的一个冰洞里……”
“还有个凡间男子,他跪在地上求我,求我帮他见他亡妻一面。”
那凡间男子讲了一段故事。
有个少年,他本是高高在上的城主府公子,可是在六岁那年,司巫叛变,借助神力杀死了他的母亲,囚禁了他的父亲,而他也被迫沦落他乡。直到有一日,故乡的商队终将他带回。
可是没有人记得他,他是城主府里最下等的奴隶,隐姓埋名,不得不蜷缩在拳脚之下。如果不是那日经过树下,他被从树上掉下的小女孩恰巧砸晕了过去,那么或许他已经死在了那个冬天。
小女孩叫阿阮。
她救了他。
然后他多了一个小尾巴。
他爬树,她在树下为他鼓掌;他泅水,她在岸上为他鼓掌;他打鸟,她站在他身后亦步亦趋,见他回望便拼命鼓掌;他烤鱼,她坐在旁边偷偷咽口水……
他将焦黑的鱼递给她,她却立刻眉开眼笑起来,可咬了一口之后,又紧紧地皱起了眉头。
世间这么多无趣的事情,可是她却能笑得这样开心。他那颗被仇恨淹没的心,终于又开始自由跳动。
如果不是小女孩的母亲轻描淡写地将他送走,如果不是他父亲曾经的部下找来,或许他和她的命运依旧是低贱的奴隶,和高贵的小姐。
他们短暂的相会,然后云泥作别。
7
“其实故事讲到这里时,我已预见了悲剧的色彩。”阿幸无意识地摩挲着食指头,笑了笑:“我便劝他,若有不甘,便往生死九渡口走一走,今生缘浅,来世再续。”
“他怎么说?”
“他拒绝了我。”阿幸轻轻叹了一口气:“他说,这是他欠阿阮的。”
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那个名叫“阿阮”的小女孩已经长大。她承了她母亲曾抛下的责任,重任玉萝城司巫之职。祭神大殿上,按照他所算计的那般,他在刺客的手中救下了她,而她也因此爱上了他,一心想嫁给他。
哪怕她的母亲软硬皆施地劝阻,哪怕他的爱意是那般阴晴不定。
她坚信着这都是彩虹前的风雨,可是到最后,她等来只有绝望。
她的大喜之日是她母亲掐算出来的吉日良辰,她盛妆喜服站在花神殿的玉萝神树下等她的裴郎,可是她的裴郎正在率兵杀入她的家。她被簇拥着逃命,惶惶回头的最后一眼,却是城楼上,她的裴郎冷冷地斩掉了她母亲的头颅。
她盛装喜服苦等新郎半日,等来自己死期。
从此她有多爱他,便有多恨他。可是恨意却没能杀死她的仇人,却令她绝望自刎。
阿幸淡淡地笑了:“他想见的人和我一样,都是没有来生的人。他若是真的想弥补她,只是见她又如何?不若以命换命,以魂换魂,溯世重生,她生他死,这才是公平。”
芙白的眉头慢慢蹙起,伸手探上了阿幸的额头,触手滚烫。若是她目能见,便能发现那双黑白分明的杏子眼底,如今布满血丝,如同玉瓷红痕。
“阿幸,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阿幸不置可否地笑了,说不出的意味深长:“而我已经醒来了。”
越三年,玉萝城城主与宣南城二公子成亲,结两城之好。 (原标题:《千灯集:溯世灯》)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