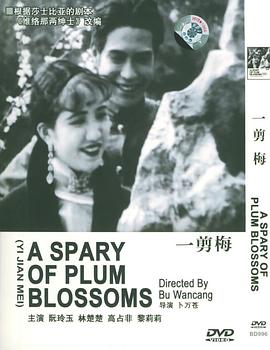剧情介绍
北京。
1957年6月30日晚,一辆轿车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宿舍大院,不一会,院里走出一老一少父子两人,上了汽车,车子驶向府右街,穿越怀仁堂,北折进入中南海甲区,在游泳池畔停住。
这里是毛主席夏季办公和暂住的处所。
卫士通报后,毛主席立刻迎接,握住老者的手说:“冒先生,欢迎你!”随后问年轻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
“舒湮。舒展的舒,湮没的湮。”年轻人回答。
原来,老者叫冒广生,时年84岁(周岁),舒湮是其子,时年43岁。
冒广生,字鹤亭,号疚斋,江苏如皋人,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诗人、词家和有精湛造诣的汉学家。1894年被清廷录为举人,担任刑部及农工部郎中;民国时期,历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会长、江浙等地海关监督;抗战胜利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南京国史馆纂修;新中国成立后,被陈毅市长特聘为上海市文管会特约顾问。
说起缘由,冒广生这次获毛主席接见,还与陈毅有关。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居住在上海的冒广生为旧时文史职员,虽学问渊博,但政府无暇顾及安置,失去工作的冒广生生活一时陷于困境。
由此也可见冒广生为官清廉,虽然在清朝、民国做官,一旦失去工作,生活就陷于困境,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朝,做官如此,人品可鉴。
1950年7月,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得知冒广生生活情况后,特聘冒广生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解决了生活问题,使其安心著述研究。陈毅在调往北京前,还多次殷殷询问冒广生的生活及著述情况,使冒广生深感晚年居得其所,生逢其时,交遇知音。
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住在儿子冒舒湮家,当时冒舒湮家在中国人民银行任专门委员,负责《中国金融》的编辑工作,全家住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宿舍大院。来京后,冒广生致书已是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亲笔信邀请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阐明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导思想、主题,以及具体要求、方法步骤等。《指示》指出,几年以来,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根据这一指示,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13 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各级党政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也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群众意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迅速进入高潮。
在党的号召和鼓励下,党外人士畅所欲言。
这时,应陈毅之请,作为党外人士的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前来专访,专访文章也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两篇文章后来在海内外多家报纸上转载。
6月28日,周总理专程登门拜访冒广生,周总理临走时告诉冒广生:“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就这样,2天后,毛主席就派车来接冒广生,做事细心周到的毛主席考虑到冒广生年事已高,就吩咐由其子陪同。
在问清冒舒湮名字后,一向喜欢拿名字作话题的毛主席含笑说:“用‘湮’字作名字的很少见。”
冒舒湮解释说:“原来用‘諲’字,作恭敬解。我第一次用舒諲的笔名投稿时,排字工人误将言旁植为三点水。我心想,这样也好,免得言多必失,就此“湮”下去了。”
毛主席忍俊不禁:“这也好嘛!一开一合,对立矛盾的统一,集中于你一身了。”
冒广生介绍说:“舒湮在抗日战争时去延安,见过主席。”
毛主席端详着冒舒湮,微微皱起双眉:“时间太久,记不清啦。”
此时,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在座。胡乔木插话说:“舒湮同志38年去过延安,见到主席。”
冒舒湮是现代剧作家、影评家,曾任上海《晨报·每日电影》编辑,抗战时期就在上海编写了《正气歌》、《精忠报国》、《梅花梦》等大量抗战话剧。1938年,受《全民抗战》主编邹韬奋委托,冒舒湮等一批青年记者到延安采访,冒舒湮采访后出版了《战斗中的陕北》、《万里风云》等报告文学集,宣传抗日,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报道党与红军领袖及高级将领的作品,引起极大震动。在延安期间,冒舒湮等记者曾获得毛主席接见,由于是集体接见,所以,毛主席对冒舒湮没有印象。
毛主席听到胡乔木的介绍后,“哦”了一声,随即引导冒广生父子坐到餐桌旁。
毛主席这时刚吃完晚饭,碗筷还未及撤除,餐桌上放着一瓶起开的长白山葡萄酒。毛主席叫人再取来两只高脚玻璃杯,亲自给冒广生父子斟酒。冒广生拱手辞谢,毛主席劝说:“这是野葡萄酿的酒,老年人吃了对身体有好处。”
毛主席举杯相邀,先自干杯。冒广生见状,也一饮而尽。
毛主席卫士用托盘递上两盅盖碗茶。毛主席取过茶盅,放在冒广生面前,掀开碗盖,说声“请”,又指另一碗茶对冒舒湮说“用茶。”
毛主席看过冒广生发表的有关整风的文章,于是话题从这篇文章开始。
毛主席很赞赏冒广生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一位85岁的前清耆宿名士拥护整风,毛主席当然高兴:“老先生讲得好啊!”毛主席夸赞说,“你讲,‘如果说共产党员没得偏差,那就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爱人以德”出自《礼记·檀弓上》:“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意思是按照道德标准去爱护人。“相见以诚”出自《清史稿·贾朴传》:“与吏民相见以诚。”意思是以真心诚意相待。
经历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的冒广生则称赞说:“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冒广生继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产党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吧?”但是,冒广生也有一点顾虑:“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做争鸣也可,叫和鸣也可。”大概含有希望毛主席对于“偏激”的话语能够宽容的意思。
1951年,毛主席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毛主席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
毛主席了解到冒广生对双百方针的顾虑,郑重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毛主席随即以浅显的语言,对冒广生阐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指出:维新派在60年前提倡革新,变法失败,流了血,给了人们教训。二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倡革命,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你我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毛主席显然也看了《人民日报》记者专访冒广生的文章,知晓冒广生的过去。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在这603名举人中就有冒广生,因此,毛主席说与冒广生是“一条道路上的人”,都是为了拯救中国。
两个人正谈论着,朱德进来了。
原来,这天晚上,会见完冒广生后,毛主席还要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李维汉、吴冷西等人开会。
毛主席向朱德介绍冒广生。
冒广生喜出望外,不禁拱手道:“老朽此生得见当代两大英雄,曷胜荣幸!”
朱德连忙摆手谦逊致谢。
毛主席拿起筷子指着饭碗笑道:“英雄也靠人民的粮食生活呀!我们不是神仙,也是吃人间烟火食的凡夫。”毛主席的谦逊更实在。
冒广生指着冒舒湮说:“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主席目视着冒舒湮说:“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我们从前也在‘安内攘外’的口号下,呃、呃……”
抗战初期,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国民党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直白了说,就是先“剿共”,再排除外患。毛主席在这里将蒋介石与宋高宗并提,意即都是卖国。
毛主席博洽多闻,熟读史书,而且出语寓庄于谐。
关于岳飞被害,人们一般认为罪在秦桧。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文征明在其《满江红》一词中却独说:“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将迫害岳飞的矛头直指宋高宗。因此,毛主席说“文征明有首词,可以一读”,就是指文征明的这首《满江红》。
由此,话题又转到诗词。
毛主席谦虚地说“愿闻高见。”冒广生也就“争鸣”起来。冒广生认为,诗变为词,小令衍生为长调,不外增、减、摊、破四法。譬如,蜀后主孟昶的《玉楼春》(冰肌玉骨)是两首七绝,经苏轼的增字、增韵而成83字的《洞仙歌》。诗词贵简炼含蓄,孟昶原作本意已足,东坡好事,未免文字游戏。
毛主席风趣地说:“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了!”
冒广生继而表述对三百年来词人提倡填词必墨守四声的不同意见,认为:“拘泥太甚,则作茧自缚。写诗填词岂能桎梏性灵,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诗囚?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那时还没词谱、词律和词韵呢。我作《四声钩沉》,即在提倡词体解放。”
毛主席对这个提法很感兴趣,也有不同见解: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抑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冒广生赞同毛主席的高见:“主席讲的是。诗词既重格律,也讲遣词雅驯,力戒粗野,能兼顾而后能并美。”
毛主席这时看了看表,说:“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冒先生的著作,我希望一读为快。”
冒广生来时就有准备,忙让冒舒湮取出《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四大册递交毛主席。
毛主席接过书十分高兴。
冒广生起立告别。毛主席握着冒广生的手说:“我过几天要到外地去,希望你老明年再来北京。”
毛主席送冒广生上车,走了一段路,忽然停步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冒广生感慨地说:“现在党内整风,共产党能把这样大的国家治理得如此好,国势的强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冒广生略一思索,继续说:“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虮虱所苦,虮虱虽小,害莫大焉。共产党是狮子,不可自己生虱,请务必提防!”
毛主席侧身问冒舒湮,说没听清楚“虮虱”两个字,是否指的那种寄生于人体和动物身上的白色的小虫子?说时,毛主席用拇指捻着食指形容着。
冒舒湮回答:“是的,主席。”
红军时期,直到转战陕北,毛主席和普通战士一样,身上也生有虱子,经常“为身上几只虮虱所苦”。用拇指捻食指的动作,就是捉虱子的动作,毛主席非常熟练。到了晚年,毛主席还不忘那段身上生虱子的岁月,曾经给身边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讲过关于虱子的笑话:一个人在朋友面前捉了一个虱子,觉得不好意思,为了掩饰,就把虱子丢在地下,吐口唾沫说:我还以为是个虱子!朋友看了,从容地把虱子拾起来端详着说:我还以为不是个虱子呢!
在弄清楚“虮虱”两字所指后,毛主席赶上一步,用严肃的表情看着冒广生,右手搭着胸口说:“讲得好呀!我一定牢记在心上。”
这时,冒广生已走近轿车旁,警卫员拉开车门,毛主席伸手掩护冒广生的头顶,叮嘱:“当心脑壳!”
毛主席对冒广生的尊重和恭敬体现在细节中。
冒广生后来没能再去北京。
1959年冬,冒广生在上海病逝,陈毅电嘱上海市政府派人送去花圈,冒广生遗体葬于苏州灵岩山五龙公墓。冒广生子女谨遵父亲遗愿,将历代祖传和其毕生的收藏900多件珍贵文物,悉数捐献给上海市博物馆。后来,冒广生后人在北京植物园内樱桃沟建了一个衣冠冢,赵朴初先生为其写了碑文,1997年,北京文物局批准将冒广生衣冠冢定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声明:欢迎点赞、评论、赞赏,欢迎大家点击“关注”箫吹明月。本头条账号文章均为箫吹明月原创,受“维权骑士”保护,如对本账号文章有抄袭、洗稿等侵权行为,箫吹明月将依法维权。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果涉及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