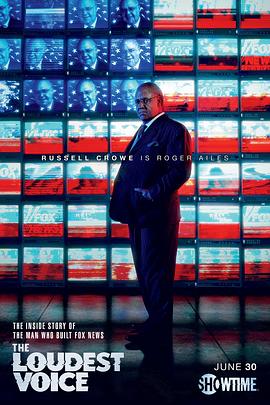剧情介绍
转眼三年的时光过去了。
小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村民们第一次缸里有了余粮。
做了辈辈农民,第一次敢放言:三年不打粮,人猪牛不慌。
我家和另外十多户人家买了电视,尽管是十二英寸的小黑白,却从此告别了喇叭时代。
自行车、缝纫机不再是稀罕物。
村里还有了五六辆“70”摩托车了。
权大妈一家的生活,除了物质上以外,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尽管有权大妈无微不至的照料,大婆在84岁的高龄去世了,老人家走的很安详,也很满足。
二儿子“在路”,和山南坡的一家闺女喜结良缘了;
次年,和二哥相差一岁的唯一闺女“在叶”也嫁给了下村。
大儿子“在道”又有了一个闺女,算是儿女双全了。
连年的丧事、喜事,花光了权大妈的钱包,也让她头上长出了白发。
然而,“在道”嫂却由于和权大妈的嫌隙,生闺女的时候,执拗的不用婆婆伺候月子。
“在道”不知道伺候,自己也没照顾好自己,落下了“月子病”。
腰直不起来,干不了农活了,只能在家洗衣做饭。
“在道”种地还是那么不靠谱,别人家缸里是满的,粮仓顶上是打尖带围子的。
他家的粮食除了上交责任田的“国粮”,也只够年吃年用。
关于他的最经典的笑话就是:当时村里流传着一句话:
你乎弄地一时,它乎弄你一年。
意思就是,种庄稼就得勤劳、操心。
打药、除草、浇水、追肥,哪一个环节都都得跟得上,才能换来一年的好收成。
所以,从整地备种开始,就得用力、用心把地扬上肥、平整好,生怕来年没有好收成。
可“在道”不在乎,他刨地是专刨打垄的那部分,其他的部分,上面有棵草,他都不动一下手。
他有自己的哲学:庄稼也不长在垄沟里,费事扒力的刨那么多干嘛?
一时成为村里的笑谈。
到了六七月份的时候,“在道”的地邻遇到了权大妈,实在憋不住了,对她说:
你去看看你儿子的地吧,草长得比玉米都高。
权大妈坐不住了,到“在道”的责任田里一看,心哇凉哇凉的:
周围邻居的地是绿油油的庄稼苗,“在道”的地里却是绿油油的草。
草丛中蜡黄羸瘦的、翘着脚尖也够不着阳光的才是“在道”的庄稼苗。
有几棵长得高点的玉米秸,被草蔓缠的已经枯死了。
草蔓娇绿的叶子,缠绕在枯死的秸秆头上,歌唱似地随风摇摆。
似乎是在炫耀,更似乎是在嘲笑。
权大妈呆不住了,赶紧回村找到“在道”。
儿子正和邻居在梧桐树下摆个小饭桌喝茶,权大妈呵斥到:你还有心思喝茶?你地里全是草你没看见吗?
“在道”不紧不慢的说:这大热的天,谁到玉米地里除草啊,那还不得憋死?
再说,怎么收点还不够吃的?你还害怕来灾年啊!
权大妈被儿子怼的绝望了,她拖着接近六十岁、早已佝偻的身躯,返回儿子的玉米地里,边哭边清理着一棵棵草。
儿子不要脸,她不能不要啊。而农民的脸,全在庄稼地里啊!
权大妈想不明白,她一辈子呕心沥血的侍奉老人,照顾丈夫,养小护小,活的没有自己,甚至把自己都舍弃掉了,她也没想换回哪怕一丝一毫的报答。
可现在,报答来了,就是儿子这一地地的草啊!
她没想到的是,这远不是儿女们最终的“报答”,她的孩子们演绎出的一幕幕悲剧,远不是她能想到的。
以后的事,听“七叶青”给大家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