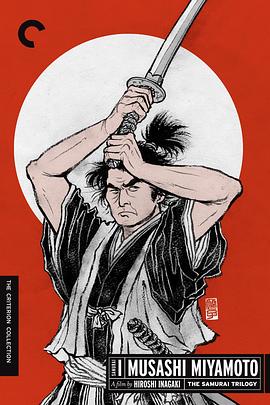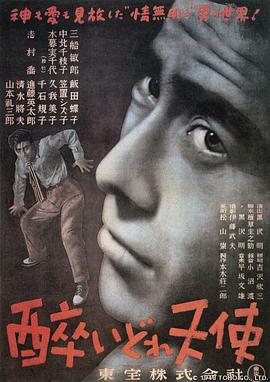剧情介绍
186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思《白痴》一书时,给他的外甥女索菲娅·伊万诺娃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及:“历数基督教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美好人物,最完美的莫过于堂·吉诃德。但他之所以美好,仅仅因为他同时也很可笑。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比堂吉诃德差远了,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但仍不失为一大创意)也很可笑,而且这一招还真管用。美好者不知自身的价值,反而遭到嘲笑,于是引起同情--由此可见,读者中也是有同情心的。同情之所以会被激发出来,正是幽默的秘密。让·瓦尔让这个人物(雨果名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也是一次精彩的尝试,但他引起同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巨大的不幸,而且社会对他不公。我要写的人物与他们毫无相似之处,绝对没有,所以我怕得要命,担心这会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毫无疑问,《白痴》是部彻底的悲剧,它以小说为体裁,却借助戏剧和史诗的表现形式,描绘出一幅19世纪俄国中上层社会腐朽势利、虚伪可笑的画卷。
这是一场无谓的救赎、自我放弃的堕落、野蛮的毁灭、肆意的癫狂。复杂的戏剧元素紧绕着人物的情绪,掀起一次次的冲突,在这场悲剧中,没有现实的苦难,没有肉体的折磨,人物需要遭受的是心灵的酷刑。
陀氏多处借助舞台剧的表现手法,不仅刻画了梅诗金公爵、娜斯塔霞、罗果仁、阿格拉娅等多个超脱现实世界的人物形象,还细致地描写了加甫里拉、伊波利特、列别杰夫等挣扎在世俗中的小人物心理,使得主人公与这类普通人的性格差异更立体形象,也使得戏剧冲突更强烈。
与同时期的俄国文学及陀氏早期巨著《穷人》、《罪与罚》等相比,《白痴》不再描绘小人物在现实中的苦难与挣扎,而是摆脱现实和经济等外部因素的约束,聚焦于中上层人物——这一类人没有饥寒窘迫的困境、没有危及生命的迫害,但讽刺的是,他们比穷人更痴迷金钱和权势,近乎病态。
而这一群体中,少数不受世俗约束,视钱财如粪土的人,内心却承受着世俗无法体会的巨大痛苦,这种痛苦使得他们精神失常、癫狂、失智、残暴、自毁。
陀氏着力描绘这种心灵的痛苦,脱离了早期的现实主义风格,以一种“贵族式的堕落”方式,撰出一曲近乎美的悲剧。
这种脱俗的取材和超现实叙事形式,也延伸至陀氏最后的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使得读者脱离现实的束缚,越过逻辑的障碍,更直接地感受到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此探索人最真实的情感和思想。
陀氏的特点之一在于用细致入骨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一特点塑造小人物时可谓入木三分,如文中对加甫里拉的描写:“尽管从头到脚浑身充满出类拔萃的愿望,然而,这类聪明的‘普通人’把自己想象成旷世奇才,可是在内心总保留着一条怀疑的蛆虫,这条蛆虫能导致聪明人最后完全绝望;纵使认命屈服,也已经被深入骨髓的虚荣心彻底毒化。”
但对于脱俗的人物,仅心理描写已经无法塑造他们非凡的人格了,他们具备更恢弘的艺术形象,需要以某种美的艺术形式展现,如画作、宗教、悲剧等。
01 可怜的骑士
作为贯穿《白痴》的脉络人物,梅诗金无疑是个脱俗的形象,陀氏以喻示的手法,将耶稣投射到他的身上,令他受嘲笑、讽刺、谩骂、迫害而毫不介怀。
如前文所述,陀氏旨在塑造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美好人物,可笑又令人同情。事实证明,陀氏的尝试不仅没有失败,某种程度上更是超越了堂吉诃德。
在梅诗金身上,没有私欲、城府、权术,他不谙世故,不明事理,却有着一颗水晶般纯净无邪的仁爱之心,是一个“完完全全美好”的人,犹如圣徒转世。
然而这么一个圣人般的形象,却身患癫痫,懵懂痴呆,自幼被视为白痴。出国疗愈后,他甫一返国就被裹入戏剧般复杂纠缠的现实里,这一场动荡波折的洗练,残酷地将他重新击为白痴。
这种自毁式的救赎,令人想到罗果仁家中悬挂的那副画作《基督在棺中》——救世主被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
结合文末受到巨大打击而失去心智的描写:“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以无限的哀伤啮噬着他的心...他终于躺到靠垫上,仿佛已经力竭精疲、灰心绝望,用自己的脸贴着罗果仁苍白、呆滞的脸;眼泪夺眶而出,流到罗果仁的面颊上。但是,他当时也许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眼泪,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
“公爵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的铺位上,每当病人发出狂叫或呓语时,就急忙用发颤的手轻柔地抚摩他的头发和两颊,似乎在对他表示疼爱,让他平静下来。但是,公爵已经完全不懂得别人问他的话,也认不出进来围在他身边的人。假如这时候施奈德亲自从瑞士赶来,对他过去的学生兼病人瞅上一眼,那么,他回想起公爵在瑞士接受治疗的第一年那种状态,现在必定会跟当年一样用手说:‘白痴!’”
读这一段时,我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一种高于悲痛的艺术美感紧紧攫取住灵魂,那一瞬间,我理解到古希腊艺术所形容的“悲剧的美”,它以画作的形式固化在人的脑海中。
也正因梅诗金脱俗的性格,陀氏在书中较少描绘他的心理活动,而是以平铺、叙事、烘托的方式塑造一名救赎者的形象,如给叶班钦一家讲述玛丽的故事、如在加甫里拉家中和娜斯塔霞宴会中的骑士行为、又如布尔多夫斯基和伊波利特上演的两出闹剧,刻画了公爵天真善良到近乎愚蠢的形象。
这种济世者形象,往往只能在狂热的信徒身上看见,这种狂热,极容易被扭曲为非人的情感,但在梅诗金身上,博爱的外衣下依然闪耀着人性的欲望。
如娜斯塔霞写给阿格拉娅的信所言:“抽象地爱人类实质上几乎总是只爱自己。”
这句话的理解,抽象地爱人类,其实只是爱自己的信仰,是接近救世主的力量;但在梅诗金身上,他关怀、原谅所有人,同时又怀着自己作为人的情感。
如他所说,在见到娜斯塔霞的那一瞬间,从她身上看到了灼热的痛苦,炙烤他的灵魂,令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她,试图将她从火海中挽救。
而后,与娜斯塔霞在莫斯科相处的那段时间里,他看到了笼罩住她的那团阴影,令她恐惧、癫狂、自毁,他因此感同身受,最初的爱意化为更深切的同情,此时他仿佛跟娜斯塔霞同处于无尽的阴暗中,不由自主地想靠近光明。
于是,他写信给阿格拉娅,那个在他贫瘠的记忆中光明的存在。
换而言之,《白痴》一书中,梅诗金一直处于冲突的矛盾激发点中,处于舆论戏剧的漩涡中心,他以高尚的品格俯瞰闹剧的荒谬,在他身上存在各种美好的品质。
如果以尼采的日神酒神二元化哲学观来解读,梅诗金无疑是日神的代表:光明、善良、美,而与之对立的酒神代表则是肆意狂欢的罗果仁和娜斯塔霞,最终日神与酒神的二元共同泯灭,同归虚无。
读者从梅诗金身上感受到悲剧之美,与尼采《悲剧的诞生》不谋而合。
02 堕落者
在罗果仁、娜斯塔霞、阿格拉娅身上,都映射出一个词语——堕落。
只是这种堕落,在罗果仁身上,是肆虐的欲望、狂暴的毁灭;在娜斯塔霞身上,是自我亵渎、不可控制的自毁;在阿格拉娅身上,是反抗式的嘲讽、天真的堕落。
三个人的身上都存在某些难以理解的元素,这些元素导致了他们同一个症状——失常,自控失常的罗果仁、精神失常的娜斯塔霞、情绪失常的阿格拉娅。
可他们失常的诱因都截然不同,我无法准确说明内在的原因。
罗果仁的诱因无疑是最纯粹的情欲,书的开头描述了罗果仁的长相:
一头鬈发几乎是全黑的,灰色的眼珠虽小,但目光炯炯。他的鼻子又大又塌,脸上颧骨高耸;薄薄的嘴唇老是撇着,现出一种狂妄、嘲弄乃至恶毒的冷笑;可是他的天庭却很饱满,轮廓端正,弥补了下颌发达得异样的缺陷。这张脸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种毫无血色的惨白,它使这位年轻人的整个面容显得憔悴不堪(尽管体型相当结实),同时还透出一股近乎痛苦的激情,这与他肆无忌惮的冷笑、傲气凌人的眼神很不调和。
这是一张充满肉欲且肆无忌惮的脸,这位富裕的地主儿子,在最初见到娜斯塔霞时,内心就被情欲牢牢地控制住,不惜反抗悭吝的老子,挥金似土为博红颜一笑,他的那种“近乎痛苦的激情”,在向娜斯塔霞表现爱意时展露无遗。
当娜斯塔霞将十万卢布付之一炬时,掀起戏剧的第一个巅峰,那金钱点燃的热焰,如炽热的欲念之火,熊熊引燃罗果仁的兽性,将他的理智燃烧殆尽。
而娜斯塔霞也在此刻纵入热焰,并陷入与罗果仁、梅诗金三人的纠缠。
书中特意省略三人在莫斯科发生的故事,读者仅能从只言片语中猜测到三人的恩怨情仇,并将远在彼得堡的阿格拉娅也拉入纷争中。
梅诗金对于娜斯塔霞的处境描述为:“可以见到她被囚禁在监狱中,头上即将落下重锤。”并对这种可预见的毁灭感到无尽的同情和恐惧。
她的痛苦,源于受到迫害后持续困扰在脑海中的黑雾,只有驱散这团黑雾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她的痛苦,并感受到这种无法治愈的疼痛。
她因此陷入自责和堕落,因为地主托茨基的蹂躏,她甚至认为自己是最罪恶的女人,并苛责梅诗金带给她的光明。
因而她的堕落,是自虐式的,无法同阴暗的过去和解,她曾经想过要以最疯狂的形式对迫害过她的人复仇,梅诗金的善良化解了她的怨恨,却无法化解她内心的伤害。
娜斯塔霞的毁灭,是对19世纪俄国阶级压迫的直接控诉。
唯独对于阿格拉娅,我始终无法理解这个娇惯的三小姐,对周遭趋炎附势的嘲讽和维护自我阶级的双面性,只能理解为陀氏塑造“双重人格”的另一形象。
在她身上,存在某种天真的未遭受迫害的理想主义,虽颇显稚嫩,但因其少见,使得梅诗金在黑雾中也想念她的光明。
另一方面,作者也有意塑造这个与娜斯塔霞有种同样美貌,却自幼被保护在象牙塔中的少女形象,以此将两者作为对比,令读者不得不思考两者迥异性格背后的原因。
03 愤世者
不管是梅诗金、娜斯塔霞还是阿格拉娅,因其过于脱离实际,我们只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心灵的煎熬,人性的光辉,却很难得到共鸣——那种熟悉的陀氏笔下宿命论的无可奈何。
但在加甫里拉和伊波利特身上,我们看到了小人物被命运束缚在现实中的痛苦和无奈。
陀氏在书中冷酷地指出,他们都是普通人,却怀揣非凡的理想,只是这种理想受限于自身的才华、现实的约束和命运的不公,他们有独特的观点,却无法形成自己的思想,往往拾人牙慧;他们艰苦奋斗,却被金钱、家庭等现实条件拖累,劳碌一生都无法接近梦想;他们自命不凡却担心自己才能不足、不折手段却在关键时刻无法完全抛弃世俗原则。
加甫里拉的痛苦,只是在追求富裕与权势失败的挫折上,是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仍旧停留在世俗意义的失败上,而伊波利特的痛苦,则是更深一层的宿命论带来的痛苦。
在《罪与罚》和尼采的“超人论”中都表现出一种哲学观念:这世上存在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凌驾于世俗的道德和法律,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他们有权利不折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肺痨缠身命不久矣的伊波利特,完全明确他不属于这一类的“超人”,他的思想也受限于生命、格局、人格,无法达到超脱,进而形成自己的“超人思想”,但他能感知到这一类层次的存在,因此他的痛苦,是认识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这种落差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伊波利特的《自白》之前,人们会认为他是个自命清高、愤世嫉俗又卑鄙无耻的青年,但在他的自白中,无论是否掺杂矫揉做作,我们总可见到这个病入膏肓的青年,对于命运的控诉。
梅诗金对于伊波利特的控诉感同身受,他想起自己患病治疗的场景:
“他面前是辉煌的天空,山下是一泓湖水,四周景物清朗,极目无涯。他望了很久,心中十分 难受。现在他回忆起,当时他曾向着这明亮、无垠的苍穹伸出双手,潸然泪下。他痛苦是因为这一切通通与他无缘。他向往已久、从小时候就一直吸引着他的常年大庆、不散筵席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始终不能躬逢其盛。每天早晨都有这般光明的太阳升起,每天上午瀑布飞泻处都有彩虹,每天傍晚远处天边那座最高的雪峰都会燃起绯红的火焰:“一只小苍蝇在他身旁一道炽热的阳光中嗡嗡地叫,它是整个这场大合唱的参加者,知道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也热爱这一席之地并感到幸福”,每一棵小草都在生长并感到幸福!万物都有自己的路,都知道自己的路,它们唱着歌儿去,唱着歌儿来;唯独他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不了解人们,不了解声音,与一切无缘,已被淘汰出局。哦,当然,那时候他说不出这些话,吐不出自己心中的块垒;他默默地黯然神伤:但现在他觉得这一切当时他就说过,说的正是这些话。”
这就是人类对于艺术、思想、美的感知力,跟有限的生命形成的天然矛盾:我们越充满爱意,越感受到自然之美,越发现超凡的思想,就越感受到宿命对于这种美好的剥削;这种残酷,对于患病者,是最直接最深切的痛苦。
伊波利特表示他曾想过学习希腊文语法,却担心还没学好就已经死了。这种头上顶着一把刀的滋味,稍微想象置身其中,就会被恐惧感攫住。
但令人绝望的是,每个人最终都需要面对这种痛苦,只是在面对它时,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态度去处理。
我时刻处于这种绝望的、未来的恐惧中。
无论如何,至少在陀翁笔下,在恐惧来临之时,我们不是孤独的。
微信公众号:inman丁